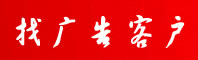广告是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适应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人类社会信息广告手段。因人类社会历史及其人类本身思维方式发展的共性,导致了中西古代广告共同的原始、自发色彩,而因中西方民族的差异性及社会历史发展的丰富个性,又导致了中西古代广告自身独具特色。
其一,因地制宜的适应性。
表现一、中西古代广告都产生于人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带。在西方,“古代世界的一切文明都围绕着地中海这个伟大的内海而诞生。它们凭借地中海互相沟通,并且四处传播自己的思想和商业”(比:享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故而服务于贸
表现二、顺应地利而传播的机灵性。西方。根据史书记载,古代的腓尼基人把贩卖的物品刻画在贸易场地两旁的山岩上,用以招引顾客。而在中国,无论是古老的敦煌莫高窟,还是悠久的大雁塔的千古记载,我们都可将其理解为一种古人用以传播文化信息的形式广告。
其二,传播形式上的窄播性。
从总体上说,由于生产力及其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的中西方广告媒介都受到很大的局限。人们更多地运用窄播如人际传播为基本广告形式。
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146年期间,古代埃及的亚历山大理亚逐渐成为地中海沿岸各民族的商业中心,有的船主雇专人在码头上大声叫喊船只泊岸时间。这种信息通知不能象今天借助发达的广播、电视媒介进行广泛的声像传播,而只能采取纯朴而原始的方式。同样地,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大街小巷的吆喝,还是磨刀霍霍的鼓动,都只能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群和地域奏效。这也是古代广告与现代广告的重大本质区别所在。
其三,标志性质广告语言的流行性。
我们不得不感叹人类思维发展的共性。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在发展中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同时难能可贵的是,在落后而漫长的古代广告阶段,中西方也都创造出了既具有艺术性,又具有趣味性,并为大众所认知与流行的丰富的广告语言。
在西方,人们从维苏威火山熔岩下发掘的古罗马城镇史迹表明,为招徕顾客,卖葡萄洒的店铺,门前挂着常青藤枝;牛厂前画着牛;饮料店前挂着水罐的把手。而异曲同工的中国古代广告中,幌子可以说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广告语言。幌子造型一般取自商品或借代物形象,使人望知取义、一目了然。烟袋铺前挂木制烟袋,鱼店前挂大木鱼,酒店挂葫芦、客店挂扫帚。诸如此类,都成为约定俗成的标志语言。
其四,对于广告形式及表现的创造性与艺术性。
艺术性与创造性是人类文明的推动力,也是广告的发展与效能的指数。无论是爽朗开放的西方人,还是含蓄深沉的中华祖宗,都在不自觉的广告实践中为了引人注目而激活着广告的形式与内容,姑且称之为古代的“广告创意”吗。
一首著名的古希腊四行广告诗句以称为西方广告创意的典范:“为了两眸晶莹,为了两腮腓红;为了人老珠不黄也为了合理的价钱,每一个在行的女人都会──购买埃斯克思斯普托制造的化妆品”而在中国古代,借助伯乐相马而成功高价售马的“名人广告”显然能代表富于哲理思辩的古代中国人的“广告创意”成功手笔。
·中西古代广告的个性·
不同的发展节拍,不同的政治文化制度及氛围的熏陶,以及不同的民族性格特征,也造就了中西古代广告的显著差别与个性。
其一:西方古代广告的张扬性与中国古代广告的含蓄能。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专职的广告人员最早是在西方而不是蕴育大文明的中国产生。如前例提到的古埃及亚历山大里亚被船主雇来喊话的人员,同时更有船主雇人穿上前后都写有船舶靠岸时间和船内所载货物名称的背心,让他们到街上来回走动。这些受雇者,被研究者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夹身广告员。而同时这种活动的广告方式,也更多地体现了古代西方广告活动的张扬性。这种张扬性也可以从古埃及所保留下来的搜寻谢姆男奴的传单上体现出来。
与雇专人四处奔波宣传与公然散发传单所对应的中国古代民间广告,则显然具有更多的东方式的含蓄。中国的行商一般都有本行业的特定广告方式,但一般都是商人自行间隙传播,而未曾见到任何雇专人广告的记载。至于公开散发传单,于中国统治者更是大逆不道,于中国伦理道德也是避之不及。即使在革命起义前,起义者为了凝聚力量,集合信徒 ,也只能偷偷将清单塞进鱼腹、肉包子,悄悄流传。对于不敢也不能采取传单散发的商人来说,他们将酒幌挂在巷子口期待借助酒的美誉度的传播造成“酒好不怕巷子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应。
其二、西方古代文字广告的纯粹性与中国古代文化广告的艺术造型。
不论是西方古代广告还是中国古代广告,都充分借助了文字的应用,这个共性前面未有提及。这里要谈的是对文字运用过程中,其艺术表现的运用程度不同。
西方字母与中国汉字在结构、书写上有显著的差别,中国文字更具有艺术性。如果说西方古代广告中,人们更多地运用文字来叙述与说理,以达到告知的目的;那么中国古代广告中的文字则具备更丰富的艺术造型及文化张力。“鸿儒”们往往对店铺酒肆所悬幌子的书法艺术有更多的注意。所以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往往有大书法家向饭肆老板赠字作匾的喜剧性结局,至于被乾隆皇上赐字一幅,高悬堂上,则不仅酒家代代兴隆,而方圆几里,也会沾光。
其三,中国古代广告的宗教性与西方古代广告的政治性
虽然古代西方宗教活动也不可避免地用到广告,如同中国古代官方也运用告知形成如诰书、策书之类来维护其统治。但笔者分别在中国古代的宗教活动与西方古代的政治活动中找到了更为纯粹的广告。相信会有更多的史料来支持这个论点的普遍意义。
据《乐府加录·文叙子》记载,“长庆中(821-824年),俗讲僧文余又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致使“听者填咽寺舍”,而寺院采取这些艺术形式的一个重要目的,据北京大学版《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者认为,是“为了招引听众,募集布施”。同样地,在中国,僧人尼姑四处云游募捐,进行宗教知识的普及讲座及本寺(庵)的知名度宣传,也是十分普遍的。
而在西方,广告很早就用于执政人员的竞选宣传中。这里是古代西方历史中的共和体制紧密相连的,而中国古代史上由于未曾形成文明时期的共和体制,故也不能出现类似的广告──可见广告的功能,无论何时,始终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其四,中国古代官方广告的形象宣传与西方古代官方广告的广告管理。
根据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提出的前提,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经济、科技、文化样样领先,作为广告这一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形式也不例外:如同今天的欧美政府对全世界进行的文化渗透一样,中国古代政府也对外进行了大规模的形象宣传,有效地塑造了泱泱大国的盛世景象及中国政府的凛然权威。
在中国各朝的记载中,都有派出大使进行本国政府美誉度传播的大量史料。而明朝郑和下西洋,更见极尽科技之先进、物产之丰富,环游列国,塑造唯我大明独尊的一次大型公关广告活动。诸如此类,当然为西方古代列国所不及。
但应该看到的是,在中国古代长期重农抑商的同时,古代西方政府在大多数阶段都尊重并鼓励工商业和贸易的发展。故而在古代西方产生了最早的法令法规(1258:《叫喊人的法则》),及其最早的广告组织(十二人小组)。
·比较之余的一点思考·
提到中西古代广告,不得不提到在媒介使用方面的技术发展问题。古代中国人已经使用喊话筒进行传播,西方没有,此为其一;古代中国自隋唐开始即发明了印刷术,蔡伦的造纸术更将中国古代的传播手段推向世界颠峰,此为其二;但今天的中国广告相对于世界广告大国,已十分落后,在我们进行大量的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是否也应该顺应我们的民族特性,书写崭新的中国现代广告个性呢?